
对克里斯·莱蒙斯来说,离开fiancée去上班比大多数人都要难。他是一名深海潜水员,通常每年都要离家几次,每次出海4周。这一次,他的工作是在苏格兰东北部阿伯丁120多英里外的北海海底更换输油管道。2012年9月的那一天,32岁的莱蒙斯准备离开时,一如既往地向他的fiancée网站莫拉格·马丁(Morag Martin)保证:“别担心。这是一个精心控制的环境。”
“我会想你的,”39岁的马丁说。“但我们会一直保持联系的。”
这对夫妇是五年前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。莱蒙斯,一个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英国人,是一名潜水员和潜水船船员。他被马丁的合群所吸引,而她却觉得他善良有趣。他们开始约会,很快莱蒙斯搬去和马丁住在一起。在他接受专业饱和潜水(SAT)培训期间,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,这是一份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维护海底管道的工作。它也有风险,从减压病到溺水——近几十年来,世界各地已经有几名SAT潜水员死亡。但马丁知道这对他有多重要。
这份工作报酬丰厚,帮助这对夫妇共同规划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未来。马丁刚成为苏格兰高地一所学校的校长,他们正在建造一座俯瞰大海的梦想之家。他们的婚礼定在次年四月。
在家里,他们的谈话范围从“招待会上我们应该用什么餐具?”到房屋地基的复杂性。
他们还谈到了生孩子,后来搬到法国,莱蒙斯在那里有家人。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

克里斯·莱蒙斯在潜水钟上。
它被称为饱和潜水,因为在深海中发现的巨大压力下,潜水员呼吸的气体会使身体饱和。当潜水员浮出水面,压力下降时,这种气体会在血液和组织中形成致命的气泡,导致减压病或减压病。SAT潜水者通过整天生活在潜水船上的加压舱中来降低这种风险。
在9月份的工作中,莱蒙斯将与另外三个团队一起在348英尺长的“托帕兹”号船上共享SAT舱室一个月。他很高兴能和邓肯·奥尔考克共事。

克里斯·莱蒙斯两侧是他的潜水员同伴邓肯·奥尔考克(左)和大卫·汤浅。
现年50岁的奥尔考克已经在北海潜水17年了。在他的前几次跳水中,他和18个月前获得资格赛资格的莱蒙斯一起工作,成为莱蒙斯的非官方导师。在一个只有短期合同的竞争激烈的行业里,奥尔考克努力让莱蒙斯在主管面前看起来不错,给他建议,让他远离错误。“如果你对某件事不确定,不要担心。我会告诉你的。”他安慰莱蒙斯。他们的第三个团队成员将是大卫·汤浅,莱蒙斯因其出色的声誉而认识他。
在会议室的头几天,男人们聊起了莱蒙斯的房子,他即将举行的婚礼,以及奥尔考克刚刚开始潜水工作的儿子。莱蒙斯不能正常地和马丁说话——舱室里的氦气使潜水员的声音又高又扭曲——但他们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,马丁给她发了骑车和爬山的冒险照片。
9月18日晚上快9点的时候,轮到莱蒙斯的团队潜水了。三人转到一艘潜水钟上,这是一艘用于深海运输的较小船只。潜水钟通过电缆降至“黄玉号”下方约250英尺的地方。莱蒙斯和汤浅将再下潜50英尺,以更换海底结构上的一些管道。这些人将通过系在潜水衣上的脐带与钟相连。这些两英寸厚的管束携带着空气、通信线路、为他们头盔上的灯和摄像机供电,以及为他们的宇航服保暖的热水——海水的温度只有39华氏度。每个潜水员都有165英尺长的救生索盘绕在钟里。奥尔考克的工作是根据需要将钓索喂给潜水员。
在水面上,风速约为35英里每小时,海水约13英尺高。虽然很粗糙,但没有黄玉不能承受的。这艘船没有固定的螺旋桨,而是有五个可以旋转的推进器。动态定位系统通过不断调整这些位置来锁定船只,因此不需要锚。奥尔考克一边为他的搭档戴上沉重的头盔,一边告诉莱蒙斯,这项工作只是例行公事。“不用着急。慢慢来。”莱蒙斯对他竖起大拇指。他感到放松、专注,随时准备出发。
对莱蒙斯来说,从钟底部2.5英尺深的洞掉进黑暗的海洋总是一个神奇的时刻。离开幽闭恐惧的潜水钟,头盔灯的灯光映照下,他感觉到失重、沉淀物和转瞬即逝的海洋生物。他和汤浅开始在管汇内工作,管汇是一个30英尺高、66英尺长的结构;它的管道和阀门控制着石油从油井流向平台。两人将用扳手和其他工具在水下工作6个小时,距离只有几英尺。

在船上,潜水主管克雷格·弗雷德里克(Craig Frederick)坐在一排控制装置和显示器前,显示器上显示着潜水员头盔摄像头的画面。他跟踪他们的进度,通过对讲机对工作的每个阶段进行指示。与此同时,在狭窄的钟里,奥尔考克坐着,周围都是仪表。他监测同事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水平,但与他们没有联系。
莱蒙斯已经工作了大约一个小时,这时他听到弗雷德里克的控制室里有声音。一个报警。也许船员在做测试?
事实上,黄玉有个大问题。弗雷德里克仪表板上的绿灯突然变成了琥珀色,然后变成了红色。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情况,弗雷德里克惊恐地想。定位系统失灵了。小船现在正在漂流,很快就会拖着潜水员一起漂流。
“放下你们的工具,回到钟那儿去。”弗雷德里克命令道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要求,莱蒙斯和汤浅开始手挽手沿着他们的脐带向结构的顶部爬去。在钟里,奥尔考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但按照弗雷德里克的指示开始拉绳子。
莱蒙斯抬头一看,原以为能看到钟的灯光,但眼前一片漆黑。然后,当他到达歧管的顶部时,他感到脐带被拉着,看到它已经绕着一块露出水面的金属。他挣扎着想解开,但结却越系越紧。这是怎么呢他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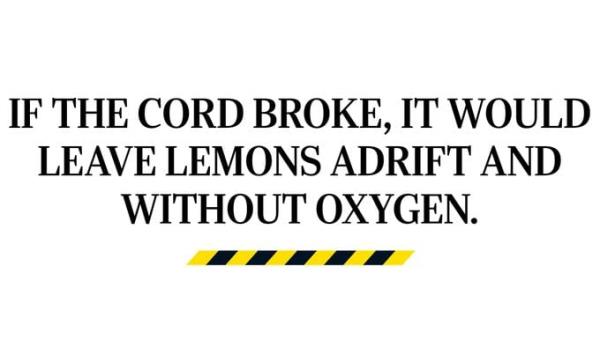
铃声响起时,奥尔考克发现莱蒙斯的绳子突然绷紧了。弗雷德里克命令道:“给潜水员2号更宽松的空间。”
“我不能!”Allcock答道。绳子不仅太紧了,还把锚从墙上拉了下来,钢支柱弯曲了,螺栓发出了呻吟声。这是不可想象的:如果绳子断了,莱蒙斯就会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漂流。奥尔考克也知道,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,如果它松动了,就会把他从钟的底部撞到水里。他迅速爬到座位上让开。但是他对莱蒙斯无能为力。
当莱蒙斯挣扎着挣脱自己时,汤浅试图回去帮忙,他的手臂在水中挥舞着。他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当汤浅的绳索把他拽走时,两名潜水员的手相距只有几码远。莱蒙斯看到汤浅脸上道歉的表情,他消失在黑暗中。
莱蒙斯加倍疯狂地试图把绳子拔下来。他听到了不祥的吱吱声,然后是空气供应线断了,接着是通信馈线。莱蒙斯无法吸气,他本能地打开了背上的应急气罐,就像他在训练中多次做的那样。几秒钟后,电缆断了,发出了像霰弹枪一样的声音。他的生命线完全断了。
莱蒙斯被甩到后面,慢慢地往下沉,他的头盔没有对讲机的声音,他的灯熄灭了,他的衣服开始冷却。他知道自己只有8分钟的氧气。
在铃声中,奥尔考克狂热地拉起松弛的脐带,希望莱蒙斯会在它的尽头。当断了的热水软管出现时,他的心一沉。然后是嘶嘶作响的空气声。他感到恶心。“我的潜水员不见了!”他对弗雷德里克喊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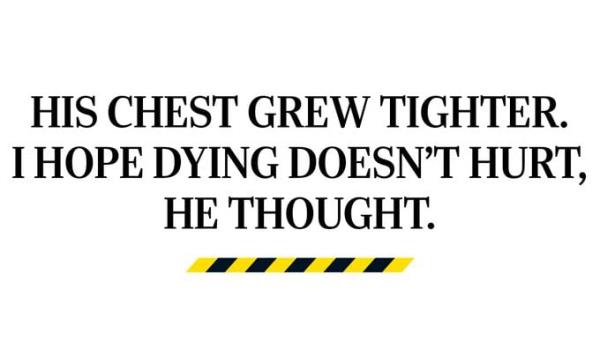
莱蒙斯在一片漆黑中挣扎着站了起来。飞船可以通过他宇航服上的信标追踪他,但他知道,如果他能设法爬到歧管的顶部,在氧气耗尽之前获救的机会就会更大。但他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如果他在黑暗中走错了路怎么办?
他几乎是随意地选择了一个方向,小心翼翼地走着,只感觉到了脚下的泥。突然,他伸出的手碰到了金属。他如释重负地抓住了它,然后开始奋力爬上建筑,喘着粗气。
到了山顶,他仍然看不到钟。一点光也没有。黄玉到哪里去了?他爬上平台,紧紧抓住金属格栅,害怕水流会把他拖走。他估计自己还剩大约五分钟的空气。他知道自己活下来的机会很渺茫。
然而,情况比他意识到的还要糟糕。船现在离我们大约700英尺远。船员们拼命地试图返回,但没有定位系统,需要两个人手动协调推进器。“黄玉”号在波浪中缓慢地曲折前进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,莱蒙斯的恐惧变成了悲伤。这可能就是我死的地方。他永远不会看到他们的房子完工,永远不会有孩子。“对不起,莫拉格!”他喊道。他的脑子里满是世俗的实际问题。她知道下一笔建筑工程款什么时候到期吗?
他大声叫着奥尔考克。“你在哪儿?”
随着氧气的减少,他的胸部越来越紧。我希望死的时候不会受伤,他想。他感到自己慢慢地陷入了昏迷。
弗雷德里克命令“黄玉号”的遥控潜水器下潜寻找莱蒙斯。它发回了他躺在金属格栅上的照片。他的手似乎在抽搐。他是还活着,还是他的四肢只是在水流中移动?距离脐带断裂已经过去了16分钟。
现在,汤浅已经回到了钟旁,准备好了,如果他们能回到原位,就把莱蒙斯找回来。弗雷德里克向他和奥尔考克汇报了船的最新进展,不过他也故意隐瞒真相,让他们振作起来。“我们快到了。”
汤浅以为他是来找尸体的。奥尔考克的思绪也暗了下来,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马丁她的fiancé不回家了。等待是痛苦的,但他努力保持希望。“我们没有忘记你,孩子。”他默默地说。坚持下去..
“黄玉”号的工程师试图重新启动定位系统,但没有成功,于是他们绝望地将其关闭,重新启动。令人惊讶的是,这奏效了。
莱蒙斯的脐带断裂已经超过25分钟了。

莱蒙斯的濒死体验,在电影《最后一口气》中重现。
最后,当船越过潜水地点时,汤浅掉了下去,发现莱蒙斯躺在他的背上。他透过莱蒙斯的面具瞥了一眼;不幸的是,里面有水。他把莱蒙斯夹在一根救生索上,开始用脐带把它们都拖上来。莱蒙斯是个大块头;这就像扛着一只巨大的海星。等他把莱蒙斯的上半身推到钟里时,又过去了六分钟。
奥尔考克解开莱蒙斯的头盔。他闭着眼睛,光秃秃的脑袋像一条牛仔裤一样蓝。奥尔考克知道,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存活那么久的可能性很小,但由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,他继续说话。“你出事了。我要给你做心肺复苏。”
他给莱蒙斯呼吸了两次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莱蒙斯突然吸了一口气。他睁开了眼睛。他眨了眨眼睛。
奥尔考克本可以跳吉格舞的。他回来了!对于通过监视器观看的弗雷德里克来说,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。“你没事吧?”他在对讲机里问道。莱蒙斯虚弱地竖起大拇指。
奥尔考克用热水冲了他的西装,然后问了他一些问题。
“你知道你在哪儿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知道你的脐带破了吗?”
“是的。”
莱蒙斯昏昏沉沉,但引人注目的是,他似乎恢复了常态。回到飞船的SAT舱后,他接受了治疗,汤浅和奥尔考克,正如奥尔考克回忆的那样,“拥抱了一下。”莱蒙斯病情稳定后,他们就去看他。还有更多的拥抱。
在接下来的三天里,当船员们在停靠在阿伯丁的“黄玉号”上减压时,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谈论着发生的事情。这有助于他们应对冲击。所有人都温和地取笑莱蒙斯的心肺复苏,说“亲吻”或亲热通常不会在潜水时进行。
莱蒙斯是如何在没有脑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的,目前尚不清楚。潜水员气体中的氧气含量是正常空气的四倍,所以他的身体可能已经被足够的氧气饱和了,足以让他继续前进。体温过低也可能使他处于关机模式,向他的器官输送氧气。
当莱蒙斯打电话给马丁时,听到她的fiancé差之千里,她吓坏了,在他从托帕兹号上下来时,她穿过苏格兰去见他。他们亲吻拥抱了很长时间。为了分散注意力,他们去看了电影,但马丁几乎没有通过她的眼泪看电影。
三周后,莱蒙斯被宣布恢复健康后,他与汤浅和奥尔考克一起回到北海去完成这项工作。“我不想失去勇气,”莱蒙斯说,他仍然是一名SAT潜水员。
“我为他感到骄傲,”奥尔科克补充道。“很多人会说,‘这太危险了。我不会再回来了。’”
第二年四月,莱蒙斯和马丁在他们家附近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婚礼。汤浅不能到场,但是莱蒙斯说:“在招待会上,人们整晚都在买欧考克威士忌。他们告诉我,‘我甚至不想和你说话,我只想拥抱你。’”
马丁回忆道:“乐队一直演奏到凌晨4点,现场一片欢腾。“人们知道这是一场几乎从未发生过的婚礼。”
莱蒙斯和马丁后来收养了一个小女孩Eubh。他们把房子盖好了。但他们的人生计划已经加快。“我们已经把房子卖了,搬到法国去了,”马丁笑着说。
莱蒙斯说:“我已经看到了死亡,我并不害怕。”“我知道我很幸运能有第二次机会。我对生活一直有一种渴望,而这次事故只会让这种渴望更加强烈。”




